编者按|本文源于一次尚未展开的观看。针对图虫OPENSEE摄影奖作品展《遥远而切近》,大门聚焦作品自述,以锐利视角剖析那些“写得太对”的语言,质问当语言先于观看,摄影究竟留下了什么。本文不仅批判自述,更深入反思当代摄影创作中语言主导的现象,提醒我们真正的观看与创作,应始于质疑与现场,而非预设的叙事框架。
如果语言先于观看,摄影还剩下什么?
评图虫OPENSEE摄影奖作品展《遥远而切近》
文/大门
读“图虫”一个摄影展览的预告,里面没有作品,只有参展者的作品自述。我原本只想翻一翻,不料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摘录几段在手机备忘录上写起了点评,越写越多,最后干脆扩写成这篇笔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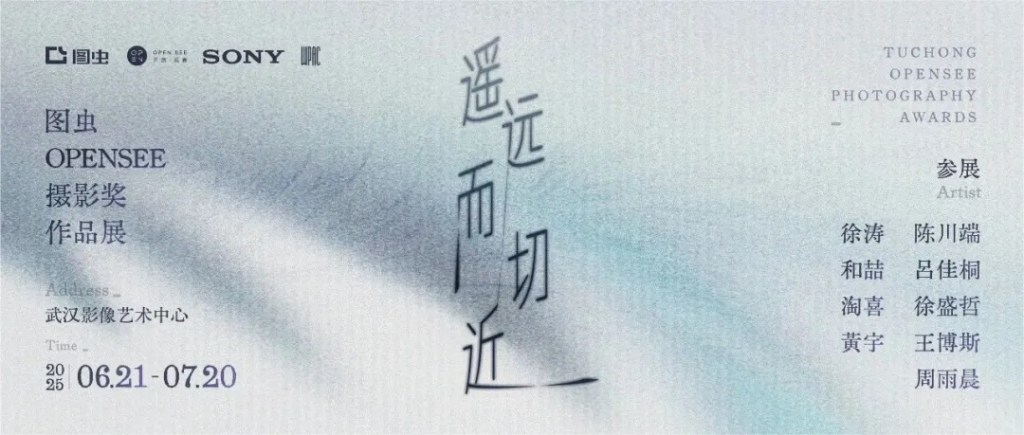
首先,我需要说明的是:这篇文章不是对作品的评论,因为我还没看到任何一张照片。所有观察与批评,都是针对“作品自述”本身——即这些作者为自己的创作所撰写的语言说明。它们不是影像,而是语言;不是观看的成果,而是观看的叙述版本。我的批评,不针对作品,只针对语言。
十几年前,我在三影堂看年度奖的展览,发现所有的作品自述都非常类似,用的词汇也差不多,当时就特意记了下来。那时博尚在草场地工作室就在三影堂对面,出门进门就到了,我看到有笔墨,就赶紧动手把它们抄录下来。那天一下午,我们的话题就是艺术家的作品自述的问题。记得当时老毛(卫东)也在,完了他还怂恿我专门为此写一篇。
只是那会儿我也还在忙着做策展,在我做的展览里,那些作品自述通常也充满了各种问题,甚至我还发现有一个作者套用一个概念时,直接把百度词条拷下来当自己的文章段落,此人后来成为中国特别有名的摄影师,满世界拿奖参展,但在我心里却一直因此看到了这个行当的浅薄和疯癫。
拖了这么多年的一篇文章,没想到竟因为“图虫”的展讯而完成了。说实话,这类阅读对我而言,完全就是一种语言耐性测试。不是因为这些文字写得太差,而是因为它们写得太对。它们太合格、太顺畅、太像艺术圈里“应该出现”的语言。这类语言不是从创作现场长出来的,而是从语言工厂运来的。
语言一旦比观看先出现,叙述就会被训练成格式化叙事;而当“共情”“身份”“记忆”这些词语开始反过来指挥经验,而不是由经验推动,那些自述就不再是创作副产品,而是一种经过自我审查后的通关密码——为策展人准备的、为审查人员准备的、为机制准备的。
我读了这九篇文字,有几篇语句优美,也有几篇写得过于干净。但真正让我警觉的,是它们语言背后那种不愿进入观看、不敢承担风险的保守。这些作品自述的最大通病是:语言比思维快,概念比问题先到场。每段话都有它的“标准结构”:
· 提一个背景(疾病、民族、边界、记忆);
· 说一段个人体验(童年、旅途、身体);
· 引出一个道德性的结论(应该被看见、被记得、被关注)。
语言像打卡,一板一眼,没有破口,也没有风险。下面我们一一来看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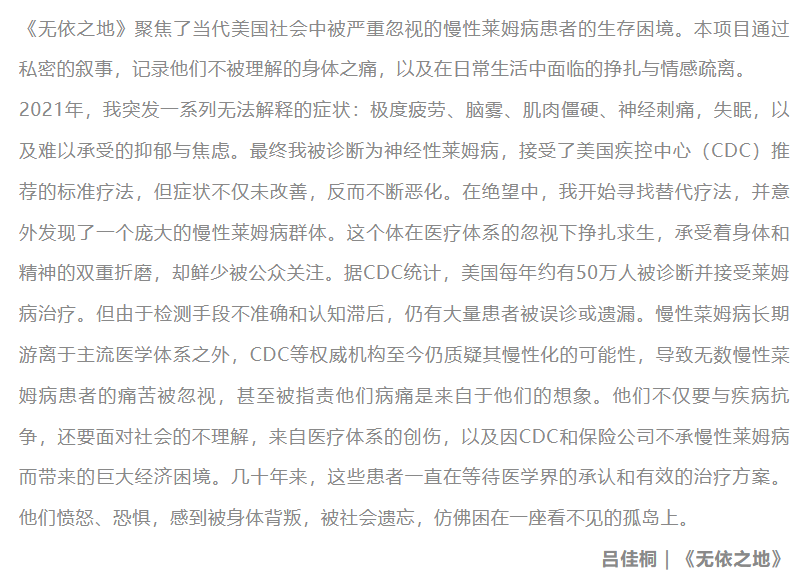
像《无依之地》,字句有诚意,议题也不错,但整段像是非营利组织的申请材料,核心是证明自己“值得被看见”。但创作从来不是资格审查。你能吃苦、有经历、有理由,这些都不构成你非拍不可的理由。那种创作者的偏执与责任,这段话里没有。
它的问题不在于表达不清,而是过于清楚地服从“正当叙事”。疾病如何被制度遗忘,这是一个好议题;但当你把自己写成一个“应当被理解与帮助的例子”,你其实让创作屈服于共情市场的逻辑,图像就变成了伦理诉求的插图。这不是观看,是求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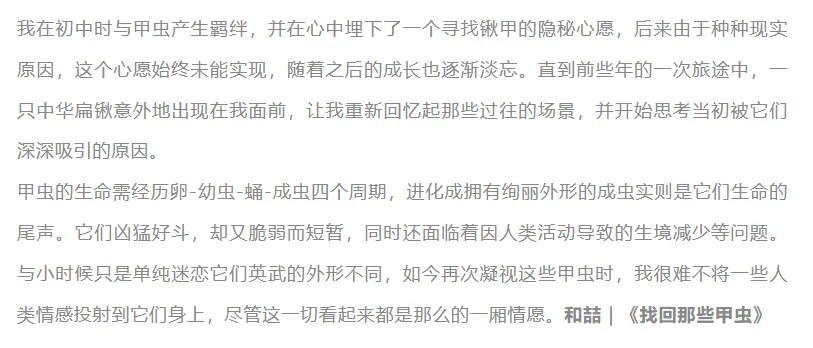
《找回那些甲虫》的自述充满了“童年的心愿”“生命的转喻”“脆弱而短暂”这类套语,看起来温柔、轻盈,实则毫无压力。这是中学生作文的语言,是感动自己的情怀,而不是构成视觉的视角。
这类文字往往将摄影与情感的关系处理得太直线:我有记忆→我拍下来→所以这是作品。但你拍的是什么?你如何处理童年的转喻?你是拍甲虫,还是拍一种被观看的符号?你如何避免重复现成的自然观?这些都没有,只留下情怀,没有观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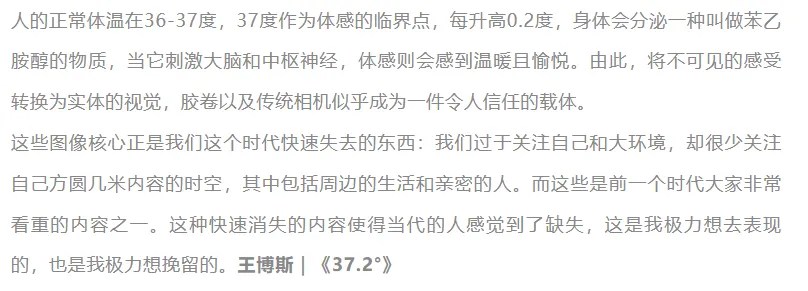
《37.2°》以苯乙胺醇与体温作为导语,语言像是摄影神经科学的包装设计。它试图构建一种生理感受与视觉信任的关联,但实际效果更像是为老派胶片情怀披上理性外衣。这不是观看的策略,而是一种糖衣叙事。冷知识的添加,只是让语气显得不那么感伤,却依然说不准、疼不到点。

《生锈的钻石》表面上是在承认困惑,实际上是在卸责。你说你拍得随意,那你就该对这个随意负责。你怎么挑选、怎么取舍、为什么留下这一张而不是另一张?“说不出来”的姿态只有在影像本身强大时才有意义,否则就是语言在帮你擦屁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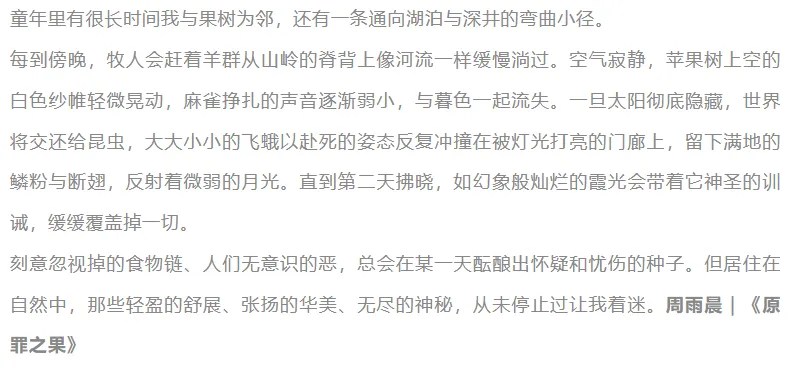
《原罪之果》的语言细腻、飘逸,像微型散文诗。它写得太准确了,准确得让人怀疑文字是否先于影像而诞生。每个形容词都像设计好的意象道具,它谈自然、罪、记忆、消逝,却没有任何一句话让人感觉作者曾真正面对过观看的挑战。这不是现场,是排练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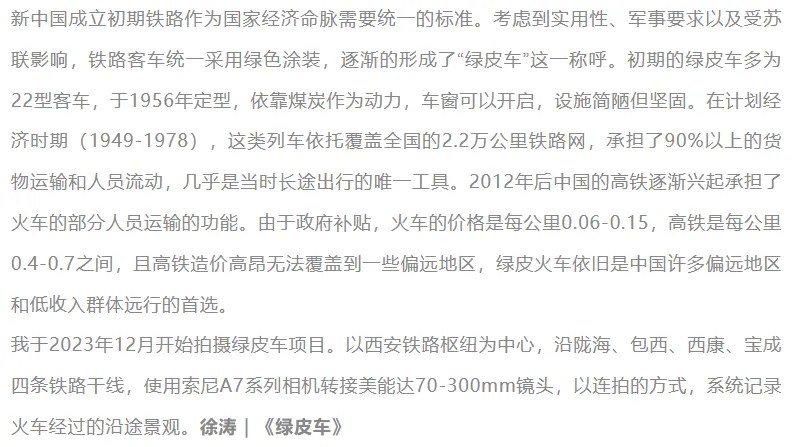
《绿皮车》的自述则是理工男式的叙事:列出年份、线路、镜头焦段,一副很踏实的样子。但你说你连拍,那你拍的是什么?运动中的模糊?车窗的节奏?还是纪实速度与观看方式的交错?你拍的是物件,不是观看。这不是观看叙事,而是摄影等于设备的假象。
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努力。我相信他们有诚意、有技巧,甚至可能有眼光。可这些语言告诉我,他们还停留在“做作品”的阶段,没有进入艺术真正复杂的结构里。他们太快学会怎么交代,而不是怎么怀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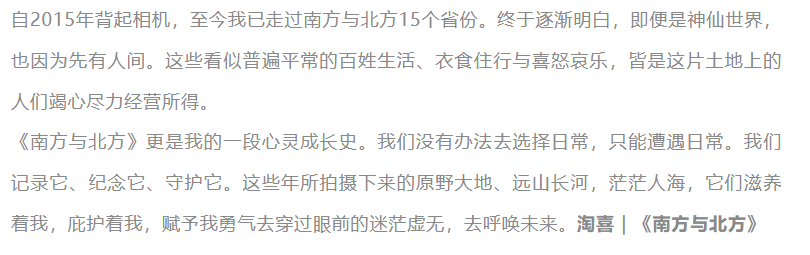
《南方与北方》语句优美,有一种田园抒情诗般的安详节奏。但也正因为它太圆润了,让我难以确定它是否真实面对过观看的结构性困难。你说“土地庇护我,万物滋养我”,那么土地是谁的?滋养的是什么?你面对的是结构性的风景,还是自我疗愈式的凝视?创作不是感恩祭,不是颂歌,而是怀疑、拉扯、破坏与再建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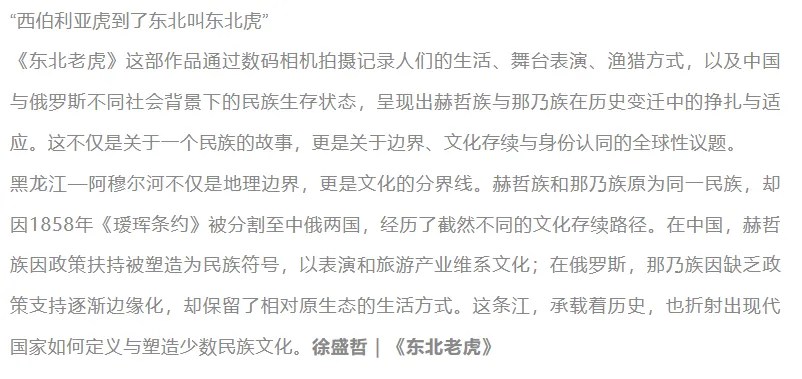
《东北老虎》是唯一让我产生进一步阅读兴趣的文本。它试图搭建政治地理的叙事对位,也试图进入边界与文化的缝隙。可惜它不够狠、不够错、不够怪。它的批评性仍然包裹在学术语气里,还没走进观看与拍摄真正的裂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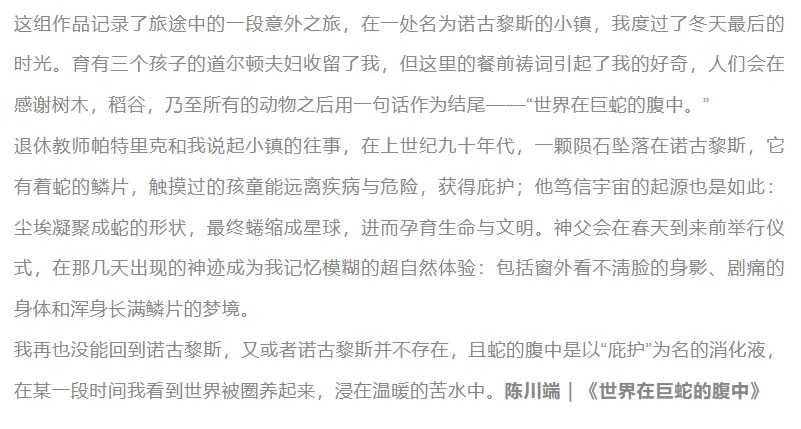
语言最讲究的,是《世界在巨蛇的腹中》。整段文字像一座小型文本装置,节奏克制、修辞完整、语调神秘、结构暧昧。它从餐前祷词绕进地理、梦境、陨石与神话。但这种语言的整洁与设计感,让观看的位置被封住。它像一段文学,却缺乏文学应有的风险;像艺术家语言,却不带艺术家的颤抖。观者无处可插,语言成了墙,不是入口。
可能有人会说:至少他们愿意写,愿意说明。总比那些什么都不解释的人强。可问题正在这里:这些语言不是“没写”,而是“写得太对”。它们符合申请格式、策展需求、展览语法,但就是没有来自观看现场的破口。它们像顺利完成的任务——唯独不是创作本身。
我想看的,不是你语言里有多少“我意识到”“我挽留住”“我感受到”,而是:
你是否曾怀疑这些照片根本不该被拍?
你是否曾面对某个影像感到语言崩溃?
你是否曾在创作里突然不认识自己?
这种语言的崩溃,不是失败,而是观看真正开始的证据。
真正的作品自述,不是说得完的故事,也不是合理的起点;而是一段语言与观看搏斗过后留下的痕迹。它不一定逻辑通顺、不一定叙述完整,但它会让人知道你曾在观看中战栗过。不是漂亮的开始,而是开始本身。
而那些写得还不错的文字呢?对不起,我真的看不出这些人是否会成为好艺术家——因为他们的语言从来没有试图说出真正难说的话。
最后,我愿再次强调:这篇文章的所有批评,仅针对作品自述的语言表现,而非作品本身。九件作品我都尚未看到,也无从对其图像、构图、观看深度或视觉表达作出判断。我能评论的,只有那些作者愿意先交出的部分——语言。语言是一种自我呈现,也是一种观看姿态的暗示。
今天这篇文章,不是对摄影作品的分析,而是一次针对语言的阅读测试,一次对艺术家在语言中如何交代自己、如何回避风险的观察与记录。
留下评论